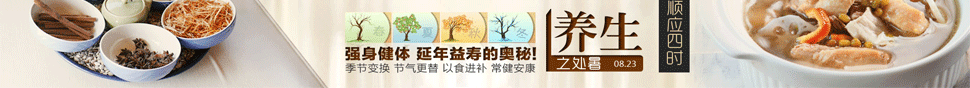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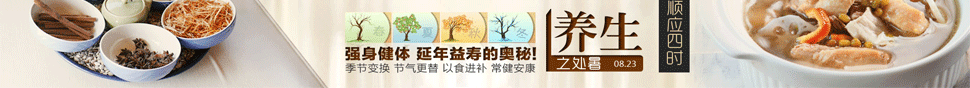
□安梁
忽必烈在潜邸之时,曾召见金朝遗臣张德辉,问道:“或云,辽以释废,金以儒亡,有诸?”
张德辉回应道:“辽事臣未周知,金季乃所亲睹。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,余皆武弁世爵,及论军国大事,又不使预闻,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,国之存亡,自有任其责者,儒何咎焉!”
言下之意,金朝败亡,不在倚重儒学,恰在武人干政。但这一论题深入人心,随着后金崛起,“金以儒亡”又成热点议题。
皇太极以金为戒,训诫臣属勿忘汉化与崇儒之祸:“当熙宗及完颜亮时,尽废太祖、太宗旧制,盘乐无度。世宗即位,恐子孙效法汉人,谕以无忘祖法,练习骑射。后世一不遵守,以讫於亡。”自此,“国语骑射”成为清朝历代皇帝谨记的祖宗之法,却也无力阻止满人的堕落。
时至今日,学界并不赞同将金朝败亡简单归咎于汉化与崇儒,钞法崩坏、用人不当、都城南迁、蒙古征伐皆是重要因素。不过,对儒学和科举的推崇,确实削弱了金初的勇武之气,致其败于剽悍外敌之手。在《另一种士人: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》一书里,日本学者饭山知保研究了金末名士元好问及秀容元氏家族的案例,揭示了科举制度对于金朝社会风气的柔化,某种程度上也为“金以儒亡”添加了一个注脚。
《另一种士人:金元时代的华北社会与科举制度》
[日]饭山知保著浙江大学出版社
秀容元氏是拓跋氏后裔,有史可考的先祖是北宋末年的神武军将领元谊,即元好问的高祖。宋徽宗宣和年间,神武军在山西、陕西等地征兵,元氏一族迁至晋北忻州。元谊之子、元好问的曾祖元春一度出任北宋隰州团练使,靖康末年隰州被金朝攻占,他才挂冠而去。不久,居于晋北的元氏也成了金朝子民。可见,入金之初,元氏本是武官家族,所居之地尽是“山夫谷民”,民风粗犷。究其原因,晋北武人在晚唐和五代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,他们与沙陀王朝和粟特裔突厥军事集团渊源颇深。因文学戏剧被后世熟知的“杨家将”,即杨业家族,也出身晋北武人世家。
不过,晋北尚武之风在金朝有所改变。昔日文人辈出的河南、陕西等地,因连年战争残破不堪,金朝初年战乱较少的晋北,逐渐养育了一批读书人。金世宗大定年间,朝廷正式实行科举、学校政策,免除官学生和会试合格者的差役。即便读书人不能最终进士及第,也能享有特殊待遇和社会地位。与此同时,邻近晋北的平阳地区,成为全国出版业中心,韵书等印刷物流布书肆,为晋北士人提供了极大便利。正如饭山知保指出,“秀容元氏作为士人家族而崛起,正是在这种由科举制度渗透所带来的社会变动扩大至晋北地区之时。”
元谊的孙辈,即元好问的祖父一辈,开始由尚武转向从文。元好问祖父元滋善获赐进士及第,官至柔服县丞。其弟滋新也尝试以读书入仕途,只不过“弱冠就科举,一不中,即以力田为业”。元好问的父辈多以恩荫入仕,都曾应试科举,可惜反复落第。尽管如此,元氏家族彼时已经具有文人习气,族人大多热衷收藏书画古董,每逢相聚,总要以藏品自娱。如此风气之下,晋北渐失沙陀与突厥旧俗,却成文华汇聚之地。
至于元好问,《金史》言其“不事举业,淹贯经传百家”,实则不然。元好问之父元德明早年文才闻于乡里,却屡试不中。兄长元好古聪颖过人,但两次应试均铩羽而归。自16岁参加科举,至32岁中举,元好问也经历了与多数读书人相同的坎坷。授业恩师郝天挺鄙夷重词赋、趋功利的科举,教导他“读书不为艺文,选官不为利养”。落榜之际,元好问还是难免发出感慨和哀叹,譬如“一寸名场心已灰,十年长路梦初回”,或是“五车载书不堪煮,两都觅官自取忙。无端学术与时背,如瞽失相徒伥伥”。
金宣宗兴定四年,即公元年,金朝统治风雨飘摇。在南宋、蒙古和西夏夹击之下,宣宗将都城南迁至汴京,又诛杀了权臣术虎高琪,却不能止住国运衰落的颓势。这一年,元好问赶往汴京应试,与百名晋地考生会饮状元楼。席间,他写下一段铿锵有力的文字,直面读书人“何以自处”的难题:“将侥幸一第,以苟活妻子耶?将靳固一命,龊龊廉谨,死心于米盐簿书之间,以取美食大官耶?抑将为奇士、为名臣,慨然自拔于流俗,以千载自任也?”元好问怀有名臣之志,故而选择了科举,次年他进士及第,总算半只脚踏入了仕途。
而就在百年前,元氏祖辈正为北宋征兵守边,尚是驰骋沙场的武人。对于祖辈记忆,元好问并不推重出身行伍的元谊和元春,而是追溯至更远的元结。元结,字次山,是中唐进士,也是唐代古文运动先驱,或许尤令元好问引以为傲。
对于金朝败亡,元好问自有一番认知,曾写诗感慨道:“塞外初捐宴赐金,当时南牧已骎骎。只知灞上真儿戏,谁谓神州遂陆沉。华表鹤来应有语,铜盘人去亦何心。兴亡谁识天公意,留著青城阅古今。”经历丧乱之后,在他看来,兴亡本是天意,与儒家天命观相符,并无武人习气与痕迹,金朝士人风貌可见一斑。
本文为钱江晚报原创作品,未经许可,禁止转载、复制、摘编、改写及进行网络传播等一切作品版权使用行为,否则本报将循司法途径追究侵权人的法律责任。
本文来源:钱江晚报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