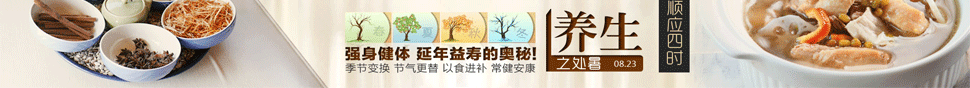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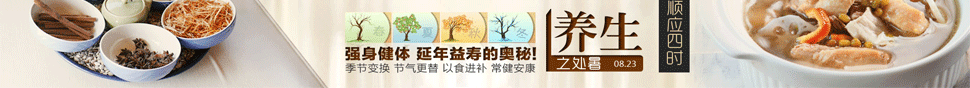
汉初宫廷伎艺及其他
——《两汉伎艺传承史论》之三
赵兴勤
摘要:两汉时期,将“礼”“乐”纳入实现政治理想的轨道而予以重新定位,这与远古之时的自娱或娱神,显然已有很大不同。两汉伎艺的重新衡定以及其自身的丰富与发展,无疑借助于这一历史演进之力。首先,汉代初期的“歌舞”对前代伎艺进行了改造,成为主要用于宗庙祭祀、殿廷宴饮等公开的大型庄重场合的集体演唱形式。其次,汉初前期的“歌唱”指在较小的范围内的一种自抒怀抱的独立演唱形式。不同类型的歌,包蕴有各不相同的思想内容。不论是群歌还是独歌,都是一种抒情手段和途径,大都系感于目下处境,即兴而发,带有较强的现实指向性。最后,“蜡祭”与“迎气”之仪反映了音乐的伦理功用不断得到强化,使伎艺演奏也充溢着浓重的政治伦理色彩。这正是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对音乐、伎艺不断渗透的结果。
关键词:汉初;宫廷伎艺;传承
作者简介:赵兴勤,男,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,主要从事汉代文学研究。
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特别令人 。
王侯秉德,其邻翼翼,显明昭式。清明鬯矣,皇帝孝德。竟全大功,抚安四极。[4]
此为几经改造后的产物,文词虽峻整华美,但内容却很是空泛,一般人难以理解。如宴娭(xī),意谓宴乐。“娭”,戏也。粥粥,敬惧貌。“粥”,读yù。聈聈,幽静也。“聈”,读yǒu。申申,从容貌。 (zhēn),通“臻”,至也。翼翼,安定而有次序。如此之类,一般人难晓其义。难怪古人称,这类立于太乐的雅乐,不过“春秋乡射,作于学官,希阔不讲。故自公卿大夫观听者,但闻铿枪,不晓其意,而欲以风谕众庶,其道无由”[4]。外在仪式的确很美,文词是雅,但在讽喻现实、纯正世风方面,却难以发挥作用,关键在于人们“但闻铿枪,不晓其意”。
但新创的歌舞伎艺,则显示出鲜明的时代特色,便于为人们所接受。如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所载,高祖十二年(公元前年),刘邦率兵平定英布之乱后,返回故乡沛县,略加逗留,“置酒沛宫,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纵酒,发沛中儿得百二十人,教之歌。酒酣,高祖击筑,自为歌诗曰:‘大风起兮云飞扬,威加海内兮归故乡,安得猛士兮守四方!’令儿皆和习之。高祖乃起舞,慷慨伤怀,泣数行下,谓沛父兄曰:‘游子悲故乡。吾虽都关中,万岁后吾魂魄犹乐思沛。且朕自沛公以诛暴逆,遂有天下,其以沛为朕汤沐邑,复其民,世世无有所与。’沛父兄诸母故人日乐饮极欢,道旧故为笑乐”[3]43-44。这一还乡悲歌之举,每每为后代诸人所感叹、称道。唐代诗人胡曾《沛宫》:“汉高辛苦事干戈,帝业兴隆俊杰多。犹恨四方无壮士,还乡悲唱《大风歌》。”[7]宋代贺铸在《歌风台》诗中,也动情地描绘出“酒阑鸣筑动云物,青襟儿曹随抑扬”①这一百余童子歌舞的热闹场景。元人陈孚也感叹:“沛宫一曲《大风歌》,谁识尊前感慨多。”②皆为刘邦的“酒酣自击筑,浩歌何雄哉”[8]赞叹不已。
刘邦的这首诗仅有三句,且每句中均含感叹词“兮”。“兮”,与“侯”通。《史记·乐书第二》:“高祖过沛,诗‘三侯’之章,令小儿歌之。”《索隐》曰:“按:过沛诗即《大风歌》也……侯,语辞也。诗曰‘侯其袆而’者是也。兮,亦语辞也。沛诗有三‘兮’,故云三侯也。”[3]即这三句,已将刘邦心忧天下、心系民生、渴望有猛士出现辅佐自己拓土守疆的磊落壮怀袒露无遗,被称为千古绝唱。早在过沛的前一年,他已患病。经过这次平叛之际的出入战阵,“病益甚”,故而想到了安排后事,感慨特多。他唱得很动情,不自觉起舞,以致“慷慨伤怀,泣数行下”,对故乡父老的系念之情也凝聚于此。围观的乡亲也大为动容,再三挽留,连住十余日。当刘邦不愿给乡亲带来太多负担,决计要走时,沛县父老又一直送到城西,“张饮三日”[3]。刘邦作为一代帝王,他的歌舞为何能唤起人们的绵绵深情,就在其紧扣当时现实,故为平常百姓所接受,“樽前洒泪数行下,当时听者翻悲哀”③。
另一则乃是汉高祖刘邦与戚夫人即兴创作的歌舞。这次歌舞,与朝廷中争立太子事有关。刘盈乃吕后所生子,高祖二年(公元前年),刘邦为汉王时,即立其为太子。因其“为人仁弱”[3],刘邦对他比较失望,“常欲废之”[3]。高祖为汉王时,曾在定陶得一戚姓女子,宠幸有加。戚夫人生子如意,也为高祖所喜,常称“如意类我”[3],遂产生以赵王如意替代太子刘盈的念头。但由于众大臣力争,刘盈的地位得以保全。高祖十一年(公元前年),英布叛。此时,刘邦患病在身,欲令太子率兵平叛。吕后采用商山四皓计,向刘邦涕泣而言,陈说原委,刘盈始得免出征,以将军监关中兵。高祖平定英布之乱,病情愈发严重,又想另立太子,且拒不听从张良、叔孙通谏言。一次,他在宫中设宴,刘盈前来陪侍,四位须眉皓发的老者紧随其后。刘邦惊诧不已,连忙打问,始知此为“商山四皓”,即:东园公、角里先生、绮里季、夏黄公,皆著名隐士。此四人在当时享有盛名,刘邦曾多次相请,但他们皆避而不见。太子刘盈用张良计,用重礼请他们出山相佐。这大大出乎高祖意料之外,由此引发出刘邦楚歌、戚夫人楚舞一幕。《史记·留侯世家》记载:
四人为寿已毕,趋去。上目送之,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:“我欲易之,彼四人辅之,羽翼已成,难动矣。吕后真而主矣。”戚夫人泣,上曰:“为我楚舞,吾为若楚歌。”歌曰:“鸿鹄高飞,一举千里。羽翮已就,横绝四海。横绝四海,当可奈何!虽有矰缴,尚安所施!”歌数阕,戚夫人嘘唏流涕,上起去,罢酒。[3]
当时的刘邦已年逾半百,身体本来就不佳,又为流矢所中,更加重了病情,自然思及身后江山托付谁手之事。他自己是以布衣持三尺剑取天下,当然希望儿子坚毅果敢似己。然刘盈性格柔懦,非如己愿。但其人已羽翼丰满,动摇不得。本来想着“终不使不肖子居爱子之上”[3],然而事情已成定局,所爱之子如意也无法替代太子,他自然深感悲哀。所唱《鸿鹄歌》就反映出这一复杂心态。戚夫人之舞,当然也弥漫着凄伤、哀怨之情。
这一歌舞,虽说未进入用于庙堂祭祀的雅乐之列,但所反映的情感却真实动人。而《大风歌》的演奏,则成了专供祭祀原庙所用的雅乐。据载,“至孝惠时,以沛宫为原庙,皆令歌儿习吹以相和,常以百二十人为员。文、景之间,礼官肄业而已”[4]。到了文、景之世,仍令礼官演习此曲。演出队伍,也保持原来面目。至今,徐州时常上演的仿汉音乐舞蹈《汉风乐舞》,序幕部分即“猛士歌大风”,“在雄浑苍劲的《大风歌》中,汉高祖刘邦统率将士征讨暴秦,铲除逆楚;将士们在大汉雄风的鼓荡下,龙腾虎跃,纵横六合。整个序幕先声夺人,气势非凡,再现汉高祖刘邦一统天下的历史伟业”[9],为传统歌舞注入了带有鲜明时代色彩的活力。
二、汉初前期的歌唱伎艺
上节既已述及歌舞,这里为何重提歌唱?因为上述歌舞乃是用于宗庙祭祀、殿廷宴饮的集体演唱形式,一般施之于公开的大型庄重场合。而此处的歌唱,则是在较小的范围内的一种自抒怀抱的独立演唱形式。“乐者,所以救忧也”[10]79,“嗟叹之不足,故永歌之”[5]。人称,舞必合歌,但歌未必有舞。何谓“歌”,《毛传》曰:“曲合乐曰歌,徒歌曰谣。”对此,朱自清《中国歌谣》辨之甚详,此不赘述。
即兴而歌是相沿已久的传统。如东汉赵晔《吴越春秋》所载古孝子《弹歌》,“断竹续竹,飞土逐宍”[11]67。《集韵》:肉,古作“宍”。此指鸟兽。虽出自后人记载,但刘勰《文心雕龙·章句》称:“寻二言肇于黄世,竹弹之谣是也。”[12]这是说黄帝之世,即有此歌。至舜,“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”[3]。尧时,又有击壤之歌。清人沈德潜《古诗源》据《帝王世纪》收录,并冠之以古逸歌之首。宋代郭茂倩所编《乐府诗集》卷八三“杂歌谣辞一”收有帝尧之时的《击壤歌》一首,引《帝王世纪》曰:“帝尧之世,天下大和,百姓无事。有八九十老人击壤而歌:‘日出而作,日入而息。凿井而饮,耕田而食。帝何力于我哉。’”④其实,击壤乃古时的一种游戏。据《太平御览》卷七五五引魏邯郸淳《艺经》:“壤,以木为之,前广后锐,长尺四,阔三寸,其形如履。将戏,先侧一壤于地,遥于三四十步,以手中壤敲之,中者为上。”⑤此歌,民间自然难以熟悉,但击壤之戏,经历代改造,易名为“打枱”,一直流行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北一带[13]25。
又据蔡邕《琴操》记载,介子推(一作绥)从晋文公重耳出奔翟,遭难绝粮,乃割腕股之肉以救重耳。重耳复国,厚赏随从其逃亡者,但却把介子推遗忘。介子推很是怨恨,乃作《龙蛇之歌》以抒情,后隐遁入山。晋文公寻访不得,乃焚烧山林,逼其出山。子推拒不出山,抱木而死。文公号泣而归。
至秦时,还出现了唱歌名家。《列子·汤问》曾记述这样一件事,“薛谭学讴于秦青,未穷青之技,自谓尽之,遂辞归。秦青弗止。饯于郊衢,抚节悲歌,声振林木,响遏行云。薛谭乃谢求反,终身不敢言归”[14]。其时,善歌者非秦青、薛谭二人,还有韩娥、侯同等人。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载:“及至韩娥、秦青、薛谈之讴,侯同曼声之歌,愤于志,积于内,盈而发音,则莫不比于律而和于人心,何则?中有本主以定清浊,不受于外而自为仪表也。”[10]《列子·汤问》还载,“昔韩娥东之齐,匮粮,过雍门,鬻歌假食。既去而余音绕梁 ,三日不绝,左右以其人弗去。过逆旅,逆旅人辱之。韩娥因曼声哀哭,一里老幼悲愁,垂涕相对,三日不食。遽而追之。娥还,复为曼声长歌。一里长幼喜跃抃舞,弗能自禁,忘向之悲也。乃厚赂发之。故雍门之人,至今善歌哭,放(仿)娥之遗声”[14]-。若所记有史实依据,那么,韩娥当是有文字记载的靠唱歌以谋生计的第一人。而且,以其歌声哀凄感人,使得许多人起而效仿,乃至形成所谓“雍门调”,这同样也是以往从未出现过的。后来,邯郸地域产生一新歌,托名著名歌手李奇,结果吸引得很多人争相效仿。当众人事后得知歌曲并非李奇创作时,便一哄而散,不再学习。这则事例说明,名人效应时常产生连锁反应,甚至可以形成一时之风尚。古今亦然。
各地之声歌,又往往互相借鉴。如中山“地薄人众”[3],“民俗懁急,仰机利而食。丈夫相聚游戏,悲歌忼慨,起则相随椎剽,休则掘冢作巧奸冶,多美物,为倡优。女子则鼓鸣瑟,跕屣,游媚贵富,入后宫,遍诸侯”[3]。而“赵女郑姬,设形容,揳鸣琴,揄长袂,蹑利屣,目挑心招,出不远千里,不择老少者,奔富厚也”[3]。时人或为“逐鱼盐商贾之利”[3]而转毂四方,“无所不至”[3];或为谋取生路,不远千里“奔富厚也”;或为躲避战乱,乃求远迁;或从军征战,羁留他乡。他们都不同程度地将故土文化裹挟而来,人称:“富商大贾周流天下,交易之物莫不通。”[3]其实,所交易的不仅仅是货物,还有各类不同文化的交流、碰撞与融合,包括带有特定地域特色的歌,进而逐渐形成自己的“乐”。正所谓“秦、楚、燕、魏之歌也,异转而皆乐”[10]。
有的歌则反映出一种舆论导向,甚而影响统治者的决策。如淮南王刘长与孝文帝刘恒同为汉高祖刘邦之子,前者乃赵王张敖美人所生。高祖八年(公元前年),刘邦从东垣过赵,赵王以美人进献,遂有身孕,生子即刘长。刘恒乃薄氏所生子。高祖十一年(公元前年),淮南王英布反。刘邦亲自率兵平乱,立刘长为淮南王。孝文帝即位后,刘长骄纵不法,为所欲为。刘恒以兄弟故,时相宽恕。但刘长不思悔改,仍我行我素,擅杀大臣,私设丞相,不用汉法,收罗亡命,“为黄屋盖乘舆,出入拟于天子”[3],遭大臣张苍、冯敬行等弹劾,遂废王号,谪往蜀郡严道(今四川荥经)。至雍(今陕西凤翔南),不食死。文帝尽封其子为侯。孝文帝十二年(公元前年),“民有作歌歌淮南厉王曰:‘一尺布,尚可缝;一斗粟,尚可舂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。’上闻之,乃叹曰:‘尧舜放逐骨肉,周公杀管蔡,天下称圣。何者?不以私害公。天下岂以我为贪淮南王地邪?’乃徙城阳王王淮南故地,而追尊谥淮南王为厉王,置园复如诸侯仪”[3]。据史书记载,是刘恒顾忌兄弟之情,对刘长过于偏袒,才使得其胆大妄为以致谋反的,并非为“贪淮南王地”。但舆论如此,人言可畏,他也只能把惩罚尺度再次放宽,不仅封身故的刘长为厉王,还分别将其儿子封王。后阜陵侯刘安被立为淮南王,《淮南鸿烈训》(即《淮南子》)就是由他主持编撰的。仅仅靠一首歌,竟然能影响到帝王的决策,作用之大,可以想见。
然,歌多用于自抒其怀。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载:
项王军壁垓下,兵少食尽,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。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,项王乃大惊曰:“汉皆已得楚乎?是何楚人之多也!”项王则夜起,饮帐中。有美人名虞,常幸从;骏马名骓,常骑之。于是项王乃悲歌忼慨,自为诗曰:“力拔山兮气盖世,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,虞兮虞兮奈若何!”歌数阕,美人和之。项王泣数行下,左右皆泣,莫能仰视。[3]38
汉军围困项羽于垓下,四面作楚歌,是以楚地之歌声,唤起项羽麾下将士思乡之情,使其无心恋战而自行瓦解,这是一个斗争策略。而项羽的悲歌慷慨,歌“力拔山兮”之诗,则是穷途末路之时的无奈感叹。正因为他感到前景黯淡,胜利无望,故而才有自刎乌江之举。短短一段文字,两处写及歌,但用途各异。前者是群歌,形成浓烈的楚地风习气场,使将士坠入强烈的思乡氛围之中;后者是独唱,是以凄越的声调自述英雄末路之怀抱,纵然豪气盖世也无力挽回颓局,只能望天悲鸣,徒唤奈何!
还有,《汉书·外戚列传》载:
高祖崩,惠帝立,吕后为皇太后,乃令永巷囚戚夫人,髠钳衣赭衣,令舂。戚夫人舂且歌曰:“子为王,母为虏,终日舂薄暮,常与死为伍!相离三千里,当谁使告女?”太后闻之大怒,曰:“乃欲倚女子邪?”乃召赵王诛之。使者三反,赵相周昌不遣。太后召赵相,相征至长安。使人复召赵王,王来。惠帝慈仁,知太后怒,自迎赵王霸上,入宫,挟与起居饮食。数月,帝晨出射,赵王不能蚤起,太后伺其独居,使人持鸩饮之。迟帝还,赵王死。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,去眼熏耳,饮瘖药,使居鞠域中,名曰“人彘”。[3]
以戚夫人受宠之情状,真有将吕后取而代之之势。然而,因刘邦去世,虽说她的儿子暂立为王,但其本人却沦为阶下囚,被剪去头发,以铁圈束颈,穿起囚徒才穿的赤色衣,做起舂米粗活。她的歌,是皇室内部强硬势力高压下的一曲哀鸣。不料,也正因为这样一首歌,不仅令她受到种种非人的摧残,而且,其子赵王如意也被毒死。一曲歌,记述的是一段悲惨的史事。
如此看来,在古代,不同类型的歌,包蕴有各不相同的思想内容。不论是群歌,还是独歌,都是一种抒情手段和途径,大都系感于目下处境,即兴而发,带有较强的现实指向性。古人称:“乐,听其音则知其俗,见其俗则知其化。”[10]87则道出这类歌唱的某些特征。
三、“蜡祭”与“迎气”之仪
传统社会以农耕为主,所以祭仪、歌舞大多离不开这类内容。四时八节,均有相应的活动。如立春、耕种、先蚕、立冬、冬至、立夏、立秋、请雨、土牛等,均为汉代祭礼活动的名目。至后来,各类活动更为密集,如清明、中秋、祀灶、龙王、风伯、雨师、雷公、电母之类,皆有相应活动予以庆祝或祭祷,虽名目繁多,但多与农业生产有一定关联。
这里先说蜡(zhà)祭。据《礼记·郊特牲》记载:
天子大蜡八,伊耆氏始为蜡。蜡也者,索也。岁十二月,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。蜡之祭也:主先啬,而祭司啬也;祭百种,以报啬也。飨农及邮表畷、禽兽,仁之至、义之尽也。古之君子,使之必报之。迎猫,为其食田鼠也;迎虎,为其食田豕也,迎而祭之也。祭坊与水庸,事也。曰:“土反其宅,水归其壑。昆虫毋作,草木归其泽。”皮弁素服而祭。素服,以送终也,葛带、榛杖,丧杀也。蜡之祭,仁之至、义之尽也;黄衣黄冠而祭,息田夫也。野夫黄冠。黄冠,草服也。[15]-
这里所描述的是上古之时的蜡祭情景。伊耆氏,乃很早的一个部落。南朝梁皇侃认为,伊耆即炎帝神农。据清人马骕《绎史》所附“绎史年表”,神农氏在有巢氏、葛天氏、阴康氏、朱襄氏、无怀氏之后,远在帝尧之前。亦有认为伊耆氏即帝尧者,见《帝王世纪》诸书。
这种祭祀仪式,当与农耕生产有关。所谓“大蜡八”,意谓祭八种神,即先啬、司啬、农、邮表畷(chuò)、猫虎、坊、水庸、昆虫。先啬,《疏》曰:“伊耆,神农也。”并引皇侃曰:“神农、伊耆,一代总号。其子孙为天子者始为蜡祭,祭其先祖造田者,故有司啬也。”[15]司啬,乃农神后稷。农,田官。注曰:“农,田畯也。”[15]邮表畷,孔颖达《疏》曰:“古之田畯,有功于民。邮表畷者,是田畯于井间所舍之处。邮若邮亭、屋宇处所。表田畔畷者,谓井畔相连畷于此田畔,相连畷之所,造此邮舍,田畯处焉。”[15]是指农官处所。猫虎,猫吃田鼠,虎驱野猪,故共祭之。坊,即堵水之坝。庸,乃排水的水沟。“古者祭祀皆有尸,以依神”⑥,是说祭祀的对象,由“尸”来充任,“古者尸无事则立,有事而后坐也。尸,神象也”[15]。“尸”,一般由“人”来充当。非祭祀场合,一旁站立。祭祀之时,则坐下来代表神(或祖先)接受后辈祭祀献牲。上文中的主祭者“皮弁”“素服”。“弁”,《说文解字》:冕也。即鹿皮做的帽子。《释名》称其形状如两手相合抃时,显然是顶部较尖,还腰系用葛条制作的带子,手拿榛杖,边舞动身躯,边唱“土反其宅”的歌。
据《周礼·春官·籥章》所载,这类祭仪,往往是“击土鼓,以乐田畯”[5]。有鼓乐伴奏,有歌唱,还有装扮成猫、鼠、虎、野猪等拟兽在追逐、戏闹或搏斗,场面当很热闹。之所以昆虫也在祭祀之列,是防其伤害庄稼。直至清代,还在上演演戏驱蝗的闹剧。据《嘉庆高邮州志》(清道光二十五年范凤谐等重校刊本)卷一一所引清人王安国《重建八蜡庙记》载述:
伊耆氏始为蜡。蜡首先啬,其八为昆虫。昆虫,螟蝗之属也。雍正癸卯岁春,旱蝗起。邑侯张公捕之殆尽。其有自他郡来者,民祷焉,无不应。每青畦绿壤间,飞蝗布天,乡之民童叟号呼,杀鸡置豚酒为赛,辄飞去不下,即下亦无所残。其大田而多稼者则合钱召巫演剧,锣鼓之声相闻。[16]
在全国不少地方,都曾建有八蜡庙。如山西左云之西郊,“旧有风雨八蜡坛庙,春秋享祀,岁时报赛,朝廷之祀典与民间之厘祝,用以祈有年而邀神贶者,迄今盖并举而不替也。越乾隆二十三四年,饥馑荐臻,虫灾迭至,邑侯李公玳馨轸念民瘼,相度地形,举坛 而改建之。远山拱峙,近水回抱,诚胜地也。是亦旱干水溢变置,社稷之意耳”[16]81。旧京剧戏目,也有《八蜡庙》,足见影响之大。
苏轼《东坡志林》卷二“祭祀”,叙及蜡祭之事:
八蜡,三代之戏礼也。岁终聚戏,此人情之所不免也,因附以礼义。亦曰:“不徒戏而已矣,祭必有尸,无尸曰‘奠’,始死之奠与释奠是也。”今蜡谓之“祭”,盖有尸也。猫虎之尸,谁当为之?置鹿与女,谁当为之?非倡优而谁!葛带榛杖,以丧老物;黄冠草笠,以尊野服,皆戏之道也。[17]26
无独有偶,宋人罗愿的《尔雅翼》卷二一,竟表述出与苏轼相似的看法:“盖三代之戏礼也。祭必有尸。无尸,曰奠。蜡谓之祭,则有尸。猫虎之尸,谁当为之?致鹿与女,谁当为之?非倡优而谁是。”⑦很显然,在古人的心目中,上古的蜡祭仪式,已鲜明地表现出歌与舞互相融合的趋势,具有了表演伎艺的某些艺术特征,且倡优活跃其间,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扮演。自古以来,诗与歌不可分,而有歌又必有舞。《毛诗序》谓:“诗者,志之所之也。在心为志,发言为诗。情动于中,而形于言。言之不足,故嗟叹之;嗟叹之不足,故永歌之;永歌之不足,不知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也。”[5]-从诗歌发生学的角度,这句话准确地道出歌、舞相伴而生这一实际。蜡祭,虽说是带有某些宗教色彩的一种仪式。但是,这一仪式的发生,与当时人们的生存环境与特定心境有关,所谓“土反其宅”的歌唱,则表现出他们对美好生活的企盼,同样是满心而发,出自真诚,故而配之以“手之舞之、足之蹈之”,便构成了一幅和谐的农耕生活画面。
至西汉,蜡祭这一仪式仍然保留。《汉书·郊祀志》曰:“祀者,所以昭孝事祖、通神明也。旁及四夷,莫不修之。下至禽兽,豺獭有祭。”颜师古注曰:“《礼记·月令》:季秋之月豺祭兽。孟春之月獭祭鱼。豺,挚搏之兽,形似狗。獭,水居而食鱼。祭者谓,杀之而布列以祭其先也。”[3]汉之礼仪,上承周、秦,故古代风习尚得以保留。又据《汉书·郊祀志》:“高祖十年春,有司请令县常以春二月及腊,祠稷以羊彘。民里社各自裁以祠。”[3]《西汉会要》卷一一“礼五”,将此祭归入“腊蜡”,并于“严延年母欲从延年腊”句后注曰:腊祭,即“今之蜡节也”[4]。可见,腊祭即古时之“蜡祭”的演化,说明蜡祭至汉依然存在。不过,很可能化繁为简,略去了歌舞之类表演。颜师古于《汉书·孝武帝纪》中仅注曰:“冬至后腊祭百神。”[3]而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也称:“季冬之月,星回岁终,阴阳以交,劳农大享腊。”[18]可知,蜡祭到了汉代徒具形式而已。
到了后来,有人认为,各地的食腊八粥,即古代蜡祭之遗绪。清康熙五十八年刻《汾阳县志》于“岁时民俗”十二月“腊八”后谓:“汉曰腊;腊者,猎也,猎兽以祭也。周曰大蜡;蜡者,索也,聚万物而索飨之也。腊祭先祖,蜡报百神,同日而异祭也。”[19]清人朱昆田《题钱舜举春郊醉社图》诗略谓:“坎坎鼓,蹲蹲舞,祈秋成,祀田祖。田祖醉,彻酒脯。速翁媪,将稺乳,相挽搂,来田头。草为茵,花为筹,酌大瓢,纷劝酬,日未落,饮不休。或皤腹,或睅目,或拍手,或顿足,或招或携或追逐,或号或呶或趜趗。葫芦颈长盛余酒,茨茹叶香裹余肉。”⑧诗既言“祀田祖”,亦似有古蜡祭之余韵。
东汉时,蜡祭逐渐被冬至或夏至之时的“迎气”之仪所取代。《后汉书·礼仪志》载:
日冬至、夏至,阴阳晷景长短之极,微气之所生也。故使八能之士八人,或吹黄钟之律间竽;或撞黄钟之钟;或度晷景,权水轻重,水一升,冬重十三两;或击黄钟之磬;或鼓黄钟之瑟,轸间九尺,二十五弦,宫处于中,左右为商、徵、角、羽;或击黄钟之鼓。先之三日,太史谒之。至日,夏时四孟,冬则四仲,其气至焉。
先气至五刻,太史令与八能之士即坐于端门左塾。大予具乐器,夏赤冬黑,列前殿之前西上,钟为端。守宫设席于器南,北面东上,正德席,鼓南西面,令晷仪东北。三刻,中黄门持兵,引太史令、八能之士入自端门,就位。二刻,侍中、尚书、御史、谒者皆陛。一刻,乘舆亲御临轩,安体静居以听之。太史令前,当轩溜北面跪。举手曰:“八能之士以备,请行事。”制曰“可”。太史令稽首曰“诺”。起立少退,顾令正德曰:“可行事。”正德曰“诺”。皆旋复位。正德立,命八能士曰:“以次行事,问音以竽。”八能曰“诺”。五音各三十为阕。正德曰:“合五音律。”先唱,五音并作,二十五阕,皆音以竽。讫,正德曰:“八能士各言事。”八能士各书板言事。文曰:“臣某言,今月若干日甲乙日冬至,黄钟之音调,君道得,孝道褒。”商臣、角民、徵事、羽物,各一板。否则召太史令各板书,封以皂囊,送西陛,跪授尚书,施当轩,北面稽首,拜上封事。尚书授侍中常侍迎受,报闻。以小黄门幡麾节度。[18]
这里所谓“八能之士”,是指撞钟者、击鼓者、吹管者、吹竽者、击磬者、鼓瑟者等伎艺之人。古人强调音乐通伦理,故认为“故撞钟者以知法度,鼓琴者以知四海,击磬者以知民事。钟音调,则君道得;君道得,则黄钟、蕤宾之律应。君道不得,则钟音不调;钟音不调,则黄钟、蕤宾之律不应。鼓音调,则臣道得;臣道得,则太簇之律应。管音调,则律历正;律历正,则夷则之律应。磬音调,则民道得;民道得,则林钟之律应。竽音调,则法度得;法度得,则无射之律应。琴音调,则四海合岁气,百川一合德。鬼神之道行,祭序巳之道得,如此,则姑洗之律应。五乐皆得,则应钟之律应。天地以和气至,则和气应;和气不至,则天地和气不应。钟音调,下臣以法贺主。鼓音调,主以法贺臣。磬音调,主以德施于百姓。琴音调,主以德及四海。入能之士常以日冬至成天文。日夏至成地理。作阴乐以成天文,作阳乐以成地理”[18]。至东汉,音乐的伦理功用不断被强化,并将阴阳五行等学说引入音乐批评,又将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普通五音,比附为君、臣、民、事、物,使伎艺演奏也充溢着政治伦理色彩,把伎艺演奏时敲敲打打之类平常行为,装饰得高妙莫测、玄而又玄。这正是汉代阴阳五行学说对音乐、伎艺不断渗透的结果。
摈除这一点不论,就钟、鼓、磬、瑟、竽的次第演奏,以及而后的“五音并作,二十五阕”而言,这一严整、规范的表演方式,以及打击乐与吹奏乐合奏的演出格局,对于艺人表演水平以及相互配合能力的提高,当有很大作用。既是“五音并作”,各表演者在音量的控制、音长的把握、节奏的转换、乐章的连接等方面,自然要慎重对待,而不能各行其是、恣意而为,应兼顾对方乃至全场的演奏。如此,才能达到五音相谐的境界。文中称“皆音以竽”,语出有据。古人称:“竽也者,五声之长者也,故竽先则钟瑟皆随,竽唱则诸乐皆和。”[20]“竽”,既为“五声之长”,众音当然应随之演奏。是竽在节制诸音的高低、长短,强调的是听命于指挥,以求音声之和谐,依然有政治伦理的意味包蕴其间。
注释
①相关讨论参见陈思编:《两宋名贤小集》卷一二〇“庆湖集”卷上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②参见陈孚:《沛县歌风台》三首之一,《陈刚中诗集》“观光稿”,明钞本。③参见李东阳:《歌风台送李舍人》,《怀麓堂集》卷七“诗稿七”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④末句沈德潜《古诗源》作“帝力于我何有哉”。参见郭茂倩编撰:《乐府诗集》第四册,中华书局年版,第页。⑤参见李昉等:《太平御览》第四册,中华书局0年版,第页。宋代王应麟《困学纪闻》卷二○、宋代车若水《脚气集》、宋代张淏《云谷杂纪》卷二、宋代高似孙《纬略》卷四、元代王祯《王氏农书》卷一四、明代周祈《名义考》卷四、明代陶宗仪《说郛》卷八○、清《钦定授时通考》卷四○、清代陈元龙《格致镜原》卷六○等,均曾叙及。⑥参见张自烈:《正字通》卷三,清康熙二十四年清畏堂刻本。⑦参见罗愿:《尔雅翼》,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。⑧参见朱昆田:《笛渔小稿》卷五,清康熙刊本。
参考文献
[1]李中华.中国文化概论[M].北京:华文出版社,4.
[2]张岱年,方克立.中国文化概论[M].北京: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.
[3]二十五史:第一册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上海书店,.
[4]徐天麟.西汉会要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.
[5]周礼注疏[M]//十三经注疏:上册.北京:中华书局,.
[6]朱熹.诗集传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.
[7]全唐诗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.
[8]钱谦益.列朝诗集:第四册[M].北京:中华书局,.
[9]孙厚兴,吴敢.徐州文化博览[M].北京:文化艺术出版社,.
[10]刘安.淮南子[M].长沙:岳麓书社,.
[11]赵晔.吴越春秋[M]//野史精品:第一辑.长沙:岳麓书社,6.
[12]刘勰.文心雕龙注释[M].周振甫,注.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.
[13]赵兴勤.中国早期戏曲生成史论[M].北京:北京大学出版社,5.
[14]严北溟,严捷.列子译注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.
[15]礼记正义[M]//十三经注疏:下册.北京:中华书局,.
[16]赵兴勤、赵韡.清代散见戏曲史料汇编(方志卷·初编):上册[M].台北:花木兰文化出版社,6.
[17]苏轼.东坡志林[M].北京:中华书局,.
[18]二十五史:第二册[M].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上海书店,.
[19]丁世良,赵放.中国地方志民俗资料汇编:华北卷[M].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.
[20]韩非.韩非子[M].长沙:岳麓书社,0.
欢迎订阅《中原文化研究》杂志
学术文章投稿:zywhyj
.
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