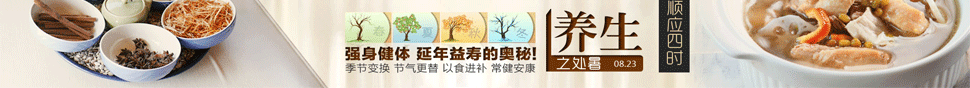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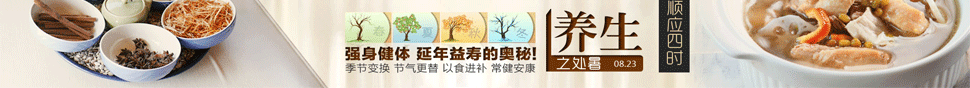
明朝弘治初年,海道副使赵鹤龄巡历威海卫,寻觅卫志而不得。当时朝廷命令纂修边卫形势事实。威海卫号称登属首卫,缺了它似乎无法交差。他只好找到卫人王悦所作的《威海赋》,从中摘取符合要求的内容,附在登州志中上呈有司。赵鹤龄曾重新修缮威海卫城池,指挥使王恺修建环翠楼以纪念。高楼蔚起,志书阙如,这多少有些遗憾。
王悦曾经著有卫志,可惜在明朝末年毁于战火。风雨飘摇,卫城的文化星火沉入黑暗。
到清朝康熙年间,朝廷命令各省府卫州县修志。因旧志而修者易,无旧志者而创之者难。威海卫无旧志可参考,威海卫守备朱孚吉深知修志之难,“捧檄而忧”,战栗不安,招集阖卫父老集思广益,但各抒己见,终难以成篇。
作志难,作卫志尤难,以卫之地为边地,卫之城为边城,卫之人民为边民也。边地者何?曰斥卤硗确(盐碱贫瘠),有耕无获,则食无所出。边城者何?曰风涛沙碛,旋筑旋颓,则人难为守。边民者何?曰卫无土著,官军之父兄子弟,凡生聚而教训者,俱为土著……
边地,边城,边民。斥卤硗确之地,风涛沙碛之城,无土著之民。以内陆的视角看边海之卫,这个地方太需要一片文化绿洲了。
康熙十三年,李标担任威海卫守备,有独立编纂卫志的想法。这时候,一个叫毕懋第的读书人出现在卫城历史上。
毕懋第,字衡南,岁贡生,威海卫人。他苦于威海无志,非常担心威海史实湮没。遂加意收集资料,在志稿首页写道:“确而有据、信而有征、切而有要”,细心考据,编修成《威海卫志》若干卷存留。
第草茅贱士,适与朱公指授之会,谨以尊闻行知者,私纂成帙,聊充蓄艾。倘博学君子不弃鄙陋俯体,礼失求野之意,枉以斧斤引之绳墨,修饰而润色之,俾之可信可传,以存威海,以存朝廷一片冲要地也……
这个“草茅贱士”,用一点一滴的努力,托起威海卫的文化光芒。
待李标来到威海时,毕懋第把卫志献上。这座城市终于有了自己的志书。虽然没有刻印成书,而仅以手抄本的形式在坊间流传,但对卫城而言,有一志书可供鉴古而知今,堪称创举。
卫有志,犹族有谱、国有史。一部志书,如果能为卫城留下哪怕一星半点儿的记忆,这座城市,就不会真正消亡。威海毕氏分老一支、老二支。两支源自一祖毕成。毕成,从军勤王,追随明太祖,四处征战,起自南巢,南至海南,西至蜀地,历时29年,为开疆功臣,授怀远将军。二祖毕文敬,奋起而光大祖功,辽东漠北,京畿江南,身上征衣杂酒痕。永乐十七()年,到任威海卫指挥同知。到了七世毕高,为毕懋第伯曾祖,一路西上南下,历登州,即墨、淮扬、兴化,闻警而动,逐倭寇而抗击,弓矢刀剑驰名异域,而蒙受冤屈,结局成谜。世爵被废,军功世家转为文化世家,后世书香绍美者蒸蒸蔚起。毕懋第的曾祖毕贵,为毕高胞弟,钻研理学,崇尚风骨,夙称一代文人,担任青苑县尉,不久即辞官归家,以渔樵自适。后移居今毕家疃,为该支毕氏一祖开枝散叶,后裔繁衍兴旺。
至毕懋第,友人称其“学富三千坟典,胸藏数万甲兵,最超群者,穿杨绝技也”,又赞他“身列儒林,技娴武备”,虽有溢美之嫌,但懋第文武全才,这是可以肯定的。而且他有侠士之风,“承先人之余绪,抱风化之夙志”,终成威海毕氏文化家族的代表人物。他以著述终身,移居白鹿屯,成为该支毕氏一祖。
追古道,念祖功,溯宗德,又创定毕氏家谱,“序功则知创业之艰难,叙德则动象贤之观摩”,后来看到毕氏家谱的后人,无不仰而倾慕,俯而深思,谆谆之意,陶冶族众敦睦风化。
他在《作谱小引》中说:
懋第幼习孔孟,少列黉门,俨然自命为书香后人者也。上之父母俱庆固己,又上之祖父祖母,皆以九旬弃世,此吾龀依膝下,长啖熊丸,赖以成人者也。其生也犹能事之,没也犹能哭之。至问高曾以上之事之人,不惟知之不明,亦且询之,无自茫然,不知先人为何许人也。呜呼,以称诗学礼之人而不知,尚可望之荷锄负耒者哉?此吾之所以痛自刻责,掩卷太息,急急乎为吾门家谱虑也。草创成编,昭兹来许,岂能如古人作述无愆,文义足法,为光裕之大观哉?亦曰常目在之,庶几见前人于楮表不至,视同气为道路也……
“在兹之托,专属我躬。”这种文化觉醒所催生的文化担当,最终使毕懋第心怀家邑,著述终身,成为《威海卫志》和《毕氏家谱》的双料创作者。如此创举,足以承前而启后。
如今,时代逢新,社会和谐,拜读康熙本《威海卫志》,毕子赤诚,跃然纸上。竖版,繁体,文言,古典似乎从未消逝。毛笔线条里,古意宛然,手泽如新。建制,沿革,分野,疆域,形势,险要……读者每每掩卷而叹,一座城市在纸上兴起。
有毕子者,威海之幸也。而以威海之山海形胜,风光秀美,物产丰饶,民风淳朴,世族辈出,毕懋第又似乎应文化之使命而生,即不出毕懋第,也会有王懋第、郭懋第。毕懋第而后,卫人郭文大又接过了如椽史笔。
毕懋第不是传说中的巨人,他只是卫城地理文化养育的普通一民。他就像卫志里那棵皂角树,扎根于卫城土地;他更像卫志里的那只鸟,呼号于古木之上,声声不绝。(王成强)

